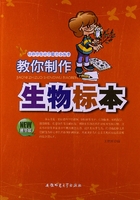突发性演出
零时廿分他走过公路卧在那里
旷野里一头枭的鸣叫
又在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
四头牛扮演四头牛
吃草的它们在剧中
有一些作为
吃草的它们的角色
总之
零时廿分他走过公路卧在那里
等待
等待着……
许多个虚点
许久
许多个许久
可是演出计划里的某些部分
应该开始的还未开始
出现的还未出现
似乎有点甚么出错了
而这是很难堪的
独自笨瓜地卧在那里
而这就叫做突发性
而这就叫做演出
甚至没有卷心菜
没有麻包袋
没有涂满甜瓜的女子
而这是很难堪的
一切都跟他们说的不同
甚至没有羽毛没有木屑
没有洋蓟没有号角
一定的
是有点甚么弄错了
他卧在那里这样想着
真的
甚至最后
落下来的
也不是他们说的那些意大利粉
而是雨
一九六八年四月
寒山及其他
“再没有寒山
再没有拾得……”
再没有甚么呢
再也没有
由于钟声的尘拂
所拂起的时间的尘埃
没有人会写道:
“寒山有裸虫……”
向无人的鸟道
散发而笑
姑苏城外
寺院的跫音呵
鸣响有如寂静的
枫桥的音色呵
某个早晨
我看见你在树下舂米
我看见你
破衣的僧人
曾经以你们的寒冷为诗
那个人今日忽然希望
把他的诗刻在
灭绝人迹的岩上了
泛满城市
一个奇异的幻象
你的扫帚
出售在一条街道转角
当我经过
白云是属于
面包铺子
甚至球场对开处
一面涂污的墙
可是我当然不会说
他们题着的是你的笑声了
昆虫咬着咬着
跛脚诗人
与乎
几万载的青天
与乎
几万载的虱子
一齐跳进转动的脑叶
忘却了
打扫食堂
而对于洗不尽的耳朵
你又如何呢
对于泉水
未说出口的话——
泉水从泉水中抽回自己
我想着泉水
然后我看见:
十灵丹和济众水的广告
一个怀孕的妇人挣扎穿过挤迫的人群
一个摔倒的孩子在路边呻吟
对于泉水
甚么是摔倒的孩子
(某个早晨
我看见你背负竹筒而去
我看见你
破衣的僧人)
再说一次:
我看见你
在没有蜻蜓的路上
举起来的手
面对黄昏杂沓的风景
我的朋友说
你以为你是那不系之舟么
一九六九年八月
面包店
风翻动杂货店的布篷
卷起地面的影子
向潮湿移过去一两寸
那以后是甚么?
柏油路上的寒光。
一个人走过面包店
依稀感到新鲜的热面包
店里的灯光照在玻璃柜上
对于从寒光的柏油路走过来的
连虚构的东西也是温暖的了。
那时曾与她走过关了门的理发店
脚踏车店和中药店
还有门缝中露出灯光的小铺
即使是这么破烂的路
那也是了不起的
那么温软的笑
那感觉
就像有一个面包夹子在胸膛里搅动
这样一起走过
不晓得该说点甚么
破烂的路也是美丽的
只是太短了
没有更多的脚踏车店和中药店
门缝中露出灯光的小铺
更不用说
那唯一的理发店
他过后就尽是这样数说
埋怨自己不知有多笨
一直走到面包店,像一个傻子
把书本递给她,然后就分手了
真使人想把头碰在墙上
你以为这是甚么
一出面包突发剧?
老兄
每天吃一个面包对你并没有甚么帮助
他最后这样下一个结论
这时他走过了面包店
灯影晃荡
向潮湿的地面移过去一两寸。
一九七一年
某打字小姐
今天的信比昨天的胖了
它们还是穿着同样的衣裳
你每天复述有一株树分期付款出售
有一朵云需要修理
以及笨重的老板
未能参加在高空举行的酒会
感到——你打错了字
又把它重打一遍——感到十分抱歉
随手把撕下的纸张扔到废纸篓去
低头时仿佛听见有点甚么在唤你
冷气机轧轧的声音
化作门的咳嗽,人的叹声
而你不晓得有些甚么
在隔邻的房间里
(总有人打错电话来
说要购买一部缝纫机)
送报的小厮端来日子的一页
你剪下葡萄的广告
存在档案里
随手也剪下一朵油墨的向日葵
去年的种籽夹在玻璃下
只开过一朵平面的花
有时你仿佛听见头上传来鸟声
一头麻雀从荧光管的壳中孵出来
拍着翅膀在那里唤你
你便会把“买”字打成“鸟”字
在冷气中打一个寒噤
随手把撕下的纸张扔到废纸篓去
那些死去的字
像飞不动的蜂尸
而你不晓得有些甚么
在隔邻的蜂房里
一九七三年
睡在沙滩上
伸手可以迎接幸福的明天
当浪变成
一颗大鲨鱼牙齿
拿去送给那位缺了门牙的朋友
一百片碎玻璃送给赤足散步的人
风灯落在口哨上
我是乡村中唯一的白痴
为甚么?
我是为
你是甚么
纯粹的游戏的
船或者屋子
买一头牡鹿给独居的牝鹿
一个岛屿给漂流的人
或者三三两两的乌鸦
那时你在这里
你就可亲眼看见它们掉进网里
转一个身 你说
我们今天这所屋子
穷得连天花板也没有
所以就不免有点太高了
只是一种沙滩
各式月亮
至于针床可笑不可笑
那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感觉了
还有甚么埋怨吗
如果说听不见夜莺
那么我只好说
各种邮递的错误
唯地址正确才可避免
有人说在月夜里
看见一个女孩乘脚踏车在波浪上经过
生起火来
被闪烁的火光感动
我们到底也不免相信了
反正夜里飞翔的天使教人不能睡眠
合掌唯有蚊子的赞叹
一九七三年
写一首诗的过程
有那么一个女孩子
打算喝掉面前这杯咖啡
然后写一首诗
苦涩如夜的黑咖啡
哼,也没有甚么了不起
还不是照样喝下去
对窗终夜的牌声响亮
街尾面摊旁的舞女和夜归男子
哗笑然后吵骂
今夜还没有人在那里打架
她给咖啡再加颗糖
加一点牛乳为了衬上杯子的颜色
并且想:那要来还未来的诗呢
抚着浅棕色的暖暖的杯
写不成又自管自笑了
偶然一辆警车驶过
醉汉去拍木料店的门
她专心注视
要写这生活的戏剧
然而甚么也没有发生
那人不疲倦么?想着
便伏在臂弯上,在纸上
画一头胖胖的猫
不行,再喝一口咖啡
透过浅棕色的杯子
看寂寞起来的街道
想最好有一点微雨
滋润这街道,并且闪光
如一朵朵在黑暗中绽开的花
她想着,再伏下去
并且睡着了
这时街上来了一辆洗街的车子
终于把街道变成潮湿
一九七三年
游戏
在这一年将尽的时光
我们来玩游戏
把糖果瓶子传过去
每人从瓶中取一颗糖
看到了最后
是谁得到一个美丽的空瓶子
以及一年的幸福
在这一年将尽的时光
我们玩砌图的游戏
每一块积木
是一块碎片
我们翻遍积木的多面
寻找一幅完整的图画
在这一年将尽的时光
我们把废纸卷成许多纸筒
用一根绳子串起来
涂上七彩的颜色
加上红色的嘴
和流苏的尾巴
做一尾快乐的蛇
拖着它上街去
在这一年将尽的时光
我们收集七彩的气球
把每一种忧愁的名字
写在上面
然后拿到热闹的年宵市场
把它们放走
这么多的颜色
糖果和积木和气球和纸蛇
这么多的碎片
串起旧的一年和新的一年
我们还在这里
把瓶子传过去
每人把手探进瓶里
谁也不晓得
最后得到的是甚么
一九七五年
听歌
她放下唱臂
就站在那里
倚着门边
而他坐在这儿
越过谈笑的人们
仍听不见声音
从黑色的盘中转出来
他看她一眼
又转过去
拿起几上的茶
她垂下眼睑
听见歌声开始流转
如夜的溽热到了尽头
破晓时吹起的微风
“我要去找一艘船
我们可以摇动它
倘若你感到
我是多么的需要你”
这歌声有时温暖
有时疲倦
有时是无奈地舒一口气
客厅的人们谈着
夏天的雨和樱桃
和一部波兰电影
其他声音
只是背景中蒙眬的字眼
只有当他回头
看见她站在门边
微笑,仰着头
他才也听见那歌
歌中说沟渠的水流飘着油污
被一把伞拌成彩虹
他看见她眼中的光彩
后来,她的眼睛垂下
唱片已转到尽头
回过头去
回答另一个人的说话
在身旁
人们都说饿了
他们说要到外面吃饭
要离去
他正在说:
“再等一会……”
这时她换上另一张唱片
声音好像飘散
流到遥远的地方
她坐在那里
想一些事情
唱片的声音转慢
如打呵欠的臂
划一个弧垂下,突然
那声音停止了
在那一片静默中,她抬起头
好像要问:
“为甚么
唱机忽然坏了?”
她走往电掣旁边
用手按插头
牵起纠缠的电线
如满心的烦忧
他回过头来
才晓得那沉默
见她按着电掣
唱机再发出沙哑的一声
一句蒙眬了的美丽的句子
像一句咽住的话
她俯下头,好像要
伏在唱片的黑色上
却并没有听见甚么
她的手在摸索中
碰到损坏的电线
漏出的电像针刺
使她的指头麻痛
到了最后
她仰起头,对这时才走过去的他
只是说:
“唱机坏了。”
然后他检验唱针
举起唱臂
并且依循纵横的电线
摸索尽头的电掣
但这并不能
使事情回转
使一个夏日发出声音
用胶布贴着电线
也无法黏回一些调子
她走回去
沉没在那端的沙发
也低头细看照片
并且说那年的事
而他在这里
拆开唱机细碎的零件
找寻一支歌
时间已经晚了
人们开始散去
吃饭,看戏
或是探访他们的表兄
真是太晚了
他们说,而她
点点头
无言地走出大门
他甚至没有说:
“再等一会……”
他低下头
手中拿着螺丝起子
甚么也没留意
仿佛只是要
把错误的校正
使沉默下去的
再放声歌唱起来
他把零件砌回原位
并回外壳
他按下掣,坐在那里等待
门在他背后
砰一声关上
这时唱片才开始旋转
歌声再一次传出来
一九七五年
抽奖
他得到一套北欧家私
他得到一个耳塞
他得到一头假发
他得到一枚浮瓜
他得到一袭睡袍
和一个跌打医生
他得到两个富有的姑母
和一头鹦鹉
他得到一副电脑
以及红橙黄绿青蓝宝
他得到公积金
佣金、礼金和帛金
他得到戏院的赠券
酒会的请卡
特别折扣的二手牙刷
他得到自动清理的文件柜
永不停嘴的闹钟
他得到两打英国人
组成的调查委员会
他得到哲学学会主席的椅子
他得到乡土艺术的专利权
他得到一只不断上升的股票
一所不断下沉的大厦
只有我
仍然两手空空
每次仰望
就仿佛听见
有人在远处发笑
迂回穿过
阴云和阵雨
撒下的骰子
是最少的点数
买了报纸
却错过渡轮
坐在码头
用香烟罐子钓鱼
在错误的火车站
等候下一班车
在高速公路上
做一匹马
她得到一个罐头丈夫
和一群电动的亲戚
她得到一套全新的指甲
眉毛和鼻子
她得到一切联会
副主席的名衔
她得到四尾会唱歌的鳄鱼
准时送花的河马
守候在街角的犀牛
可资谈论的大毛龟
她得到一个发罩
她得到两颗血淋淋的心
她得到邻居阿秀上周买的
那种吸尘机
她得到那种灰尘
她得到十二种官方承认的
大学入学试的资格
她得到所有不同牌子酱油
送出的小碟
只有我
仍然两手空空
坐在淤塞的河边
唱一支蓝色的歌
天气这么冷
却忘了大衣
空的藤椅上
己经坐着个人
围上围巾
戴上鲜花
并且投掷银币
幸运是头像
开出的是字
我们的面包
被人偷去
空的瓦瓮旁
向日葵借出还未归还
人们捧着抽到的东西
赶着跑去把奖品收藏
我仍在这里
慢慢地走
再会了先生
再会了
女士
我在后面叫
再会了
南瓜和玉蜀黍
捧着这么多东西走路
小心不要摔倒
但他们以为我要赶上去
却都跑得更快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